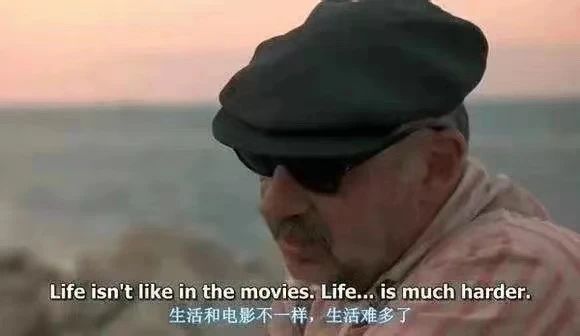「这仿佛为我们制造出一个超然的外部视角——一个不带指责、不必回应的“虚拟照护者”。」
>>>
“小人建过山车就是为了吓自己一跳。”
“有的小人定期装饰自己的指甲盖。”
“小人吃饱了就屁颠屁颠去拉屎。”
“从上帝视角看,一群小小人被苦难绊住就哭着说不活了,真的挺萌。”
(“上帝视角看人类”部分文案)
#上帝视角看人类#把生活切换到一个微缩景观中。这种抽离自身、以观察者甚至“造物主”般的视角,将人类自身(包括行为、生理、社会规则等)当作客体进行审视、描述和调侃。
比如“拿一个塑料条条假装自己的睫毛”“飞机上人类齐齐睡去又在放饭的时候都醒来好像等待喂食的仓鼠”……人类自己就像一个被投放进布景中的小小角色,一边忙碌奔跑,一边不知为何登场,而世界则像一个巨大的剧场,充满了旁观者视角、隐形剧本与NPC任务。
这类话语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。一种声音认为,这种表达方式让日常变得有趣,是在疲惫生活中的自我娱乐与解压;另一种声音则批评它是“咯噔文学”或“娇妻文学”的变体,把真实的苦难轻描淡写为“小人被绊住”,是一种对痛苦的娱乐化、对现实的逃避。
(部分网友认为“上帝视角”是“咯噔文学”)
争议的核心,其实不止是表达内容,而是我们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安放自己的情绪。“上帝视角”轻盈调侃式的表达成为一种折中的语言策略——
将“我”转化为“小人”,归于“人类”的集合体,个体既参与其中,获得了自嘲与喘息的自由;又得以抽离,在语言中虚构一个自我关照的空间,哪怕短暂、脆弱,也足以包裹当下的自己。
在“上帝视角看人类”的文案中 “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”是主线任务,其上附加小人们“自得其乐”或“崩溃叫喊”的支线任务,一切责任或身份都被暂时搁置。
微缩提供了一种抽离的观看方式。现代社会中,人类早已不再是简单的“动物”,但也没有变得“完全理性”。在以效率为核心的工作制度、充满表演性的社交期待,以及边界模糊却控制感强烈的公共空间规范的层层规训之下,我们逐渐忘记了作为一个“有机体”的生存方式:困了睡、急了跑、饿了吃。
具身性理论指出,人的情绪与意识并非悬浮于身体之上,而是与感知深度融合。当身体被迫让位于效率,思维也随之脱节,人类成为时刻运作的机器,压抑与倦怠便成为日常底色。
(真实故事计划《困在肠易激中的高中生》网友评论)
这种压抑并不少见。2020年,初中生与高中生肠易激综合征检出率分别高达13.43%与26.85%;而互联网讨论中,绝大部分网友都表明,自己在成年之后仍会在重要场合肠胃应激。这些并非真正的病,而是一种情绪和压力无法排解后的“躯体抗议”。
而在“上帝视角”下,人类被还原为“小动物”:无需解释行为,不承担责任,可以理直气壮地吃、玩、睡和崩溃。
博主@菇菇米Gugumi因“小人”和“小孩”系列视频走红。在她的“小人系列”中,小人用化妆刷扫地,在卫生纸卷上跑步,用花生米压腿健身——日常行为被微缩化处理,生活变成了冒险。
(@菇菇米“小人”和“小孩”系列视频)
她扮演的“小孩”角色则总在比划着小手,一刻不停地表达情绪:为才艺表演紧张,对酒店小牙膏着迷,打开电器时充满好奇……小孩的无聊,就是那种“总找不到地方安放的十个手指”,而这些琐碎感受在镜头中都被认真地对待。
许多成年人在观看后“安心地缓缓展开,缓缓下沉”,仿佛回到了那个牛奶打翻就要哭、发呆一整天也不会被催促的童年。某种意义上,这是一种长期被压抑的基本需求:想要被细心照顾,想要被无条件理解。
(网友对@菇菇米Gugumi的安利文案)
在更广泛的年轻一代的认知中,和猫狗相处的养宠经验也被转化为一种柔性的对照——人类意识到,为宠物准备慢食碗、设计玩具“丰容”以及每日必要的放风遛弯,其实是对它们节律的体贴;而这份体贴若回流向人类自身,则是一种迟到却必要的理解。
这套“拟物化”叙事并非没有争议。
“第一次活,手忙脚乱,一点小事就想死,是正常人类的可爱反应机制。”在赞同者眼中,这是对自己脆弱状态的宽容;在批评者看来,这无异于把真实痛苦娱乐化、可爱化,甚至带有“自嬷”的意味——用嗲萌、顺从、无害的方式包装经历,以弱者姿态把痛感处理成撒娇,以便于他人接受,同时也掩盖了应有的抵抗强度。
(部分网友认为“上帝视角”令人不适)
“自嬷”成为贬义标签,反映了当下人们对“二手情绪”的敏感。在公共空间里,我们不仅要应对自己的悲伤和崩溃,还要不断吸收他人的情绪投射。
但若将“小人剧场”的话语完全归为“自我物化”,则未免失之偏颇。它更多是一种极限情境下的情绪调适方式。文化理论中的“弱理论”主张:用低强度、碎片化、非线性的方式理解复杂现实。这种“弱姿态”并非妥协,而是一种现实下更节能的生存策略。
英国作家西蒙·加菲尔德在《把世界装进火柴盒:微缩的历史》中写道,人类对微缩世界的痴迷,包含秩序和掌控的渴望。搭建生态箱、挖蚂蚁洞、拼乐高、玩《我的世界》……这些微缩行为让我们在现实的不可控中,找到一种仿佛“造物主”的安全感。
(微型立体模型大师田中达也作品)
它不求根本解决问题,却能以最低代价缓解情绪内耗,为个体争取一点喘息的余地。但“自嬷”是否真的能抵抗现实的社会苦难?这仍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。
人们的广泛共鸣也暴露了一个事实:我们正处于一个照护机制失效的社会。无论是亲密关系、职场制度、公共空间还是情绪互助网络,越来越多的个体感到无处可逃、无处可托。
“上帝视角”没有提供什么深刻洞见,但它可以被所有人套用在任意一种狼狈、无措、微弱的处境上。人类社会千百条或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训一下子不存在了,脑袋空空,世界安静,渺小甚至轻盈。
也许,“上帝视角”是人类在现实中找不到出口时,对照护空间的一种虚构尝试。
这种语言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互联网语境中。从“娇妻文学”到“鼠鼠文学”,再到今天的“小人剧场”,我们始终在为真实的苦难寻找一种可承受、可言说的表达方式。
(“自嬷”文学)
当传统意义上的“被关心”“被照料”变得稀缺甚至尴尬,在这种情境下,语言开始承担起“替代照护”的功能。“上帝视角”便是其变体:一个抽离的、无指责的观察者,一种温和的语言策略。
娱乐式的自我观察与自嘲因此得以超越个体私语,上升为一个“从云端俯瞰”的公共表达形式。
语言虽然无法改变现实,却可能激活某些迟到的理解和体察。在鼠鼠文学中,我们理解了安陵容,也理解了“恶毒女配”;在娇妻文学中,我们读到了“晚晚”,也看见了她背后更立体的女性困境。在“养宠”过程中,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充满掌控欲的“家长”;而在“小人剧场”中,更多人第一次意识到,生活的主线其实应该是“吃喝拉撒睡”——那些一直被效率社会所遮蔽、被忽视的基本需求。
引入鼠鼠,引入时光机,引入自然生灵,引入“上帝视角”,都是一次次试图重新把握住当下的努力。它们消解的不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,也是在消除一种深藏的自我审判:脱离了表面的感动、想象与厌弃之后,我们或许终于可以试着温柔地看待自己。
(@走进奶牛猫是bot类博主,其投稿大多以奶牛猫的语气对“人朋友”说话。)
这或许就是“上帝视角看人类”的真正功能所在:在这个情绪持续外溢、照护机制不断失效的时代,它为疲惫的个体腾出了一点点喘息的缝隙,让我们既不必时时坚强,也不至于完全崩溃。
当自我叙述越来越困难时,一句“人类太好笑了吧”既不是嗲,也不是媚,而是一层轻轻落下的壳。
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。但人类真正的能动性,并不止于抽离,而在于来回切换视角,重新回到生活本身。
(图片来源于网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