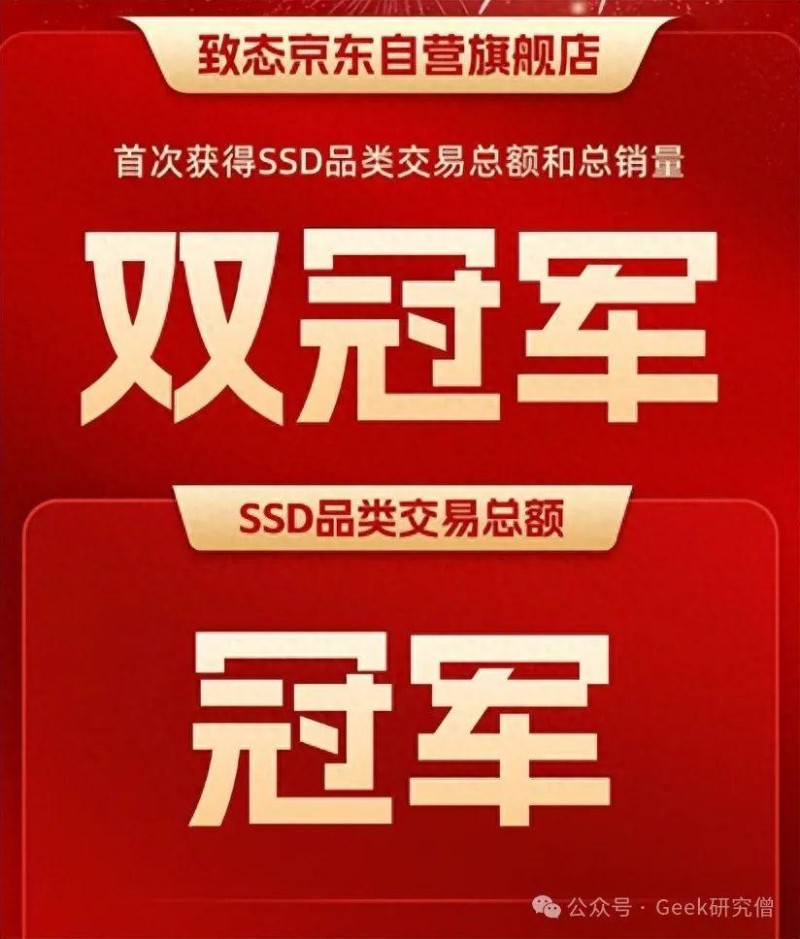1937年冬,南京城被入侵日军占领...
刀影与火光中,普通市民王广海为了求得生存机会,成为了日军驻南京部队的翻译官。
在此期间,他亲眼目睹了同胞们惨死脚下的情景,甚至其中还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...
听着那一声声屠戮哀嚎,他却始终沉默如石,佯装麻木,扮演好一具会呼吸的木偶,才能苟延残喘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所有角色皆有自己的人物弧光和成长线,唯有王传君饰演的王广海不配拥有!
同样都会说日语,关谷神奇已不再神奇!
他并非传统抗日叙事下的脸谱化Han奸形象...
而是一个在绝境中不断进行自我催眠自我欺骗的求生者,用职业身份麻醉良知,以投机姿态换取生存,却在人性底线反复挣扎的…这样一个角色。

王广海他并不完全是一个百分之百恶的人,但绝对是一个烂人,争议点就在此处...
网友们真没必要替他洗白!
最后被一枪毙命,是对他的善待,也是一种解脱,如果按照传统抗日片去演,那王广海肯定要死得更惨一点,才能平民愤啊。
不过,有争议,才值得去讨论嘛...
有的观众认为贪生怕死那是人之本性,从隐忍到爆发需要时间积累,王广海老婆孩子被杀是起点,屠城是过渡点,而深爱的毓秀即将被日军侵犯时,正是压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临死前那句脏话,完善了人物的反抗之路,角色此刻得以升华!
因为这一刻,角色有了良知,有了民族情义。
对于王广海,你们真是这样解读的吗?他真值得我们去共情吗?

在我个人理解中,答案是“不”!他并没有!
从王广海在片子里经历的几幕关键场景,我们可清晰洞见这个人物的心理走向...

比如摔婴事件,王广海目睹日军残忍行为,表情充满了难以掩饰的痛苦。
但为了生存,他立刻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。
他拿起喇叭,强作镇定高喊:他只是晕了。并催促大家笑一笑,要拍照了...
这一幕极其残酷地展现了他为了活下去,如何强迫自己扭曲认知,粉饰太平,将巨大冲击压抑下去,这既是欺骗民众,更是欺骗自己。
他自诩不是Han奸,是翻译,将服务日军美化为职业行为,甚至幻想与日方建立平等关系。

他和伊藤秀夫对话, 总强调“我们是朋友”,借此来获取生存特权与心理安慰...
这不就是典型的奴役者自我欺骗行为嘛。

再比如毓秀两次追问“他们会输吗?我们有未来吗”?王广海如何回答的?
怎么会输!人都死没了谁和他们打!那一语双关的绝唱质问让情感压抑达到了爆发临界点。
王广海向毓秀坦白了自己的生存逻辑,因为看不到胜利希望,所以选择苟活...
和对方成为朋友也是试图想保全身边人。
而对无法控制之事则选择视而不见,这套逻辑是他赖以生存的心理防御机制。

另一层面,毓秀问我们有未来吗?既指两人暧昧关系,亦暗喻民族命运...
但王广海想不到那么长远,他目前所做的这一切,只希望和毓秀能有一个美好未来。
所以,当毓秀被侵犯时,他长期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,之前连妻儿被杀都沉默退缩的他,此刻却因最私密的情感纽带被践踏而爆发。
为爱赴死看似英勇,实则是绝望下的本能反抗,他终究未能超越个人情欲,将其上升为民族大义。

而临死之际的痛骂,让他找回良知了吗?
与其说是良知,不如说是“想当人”的瞬间冲动所致,那一刻狗咬主人的嘲讽彻底显形...
他至死都被视为工具,从未获得“人”的尊严,他的爆发更像是一种绝望宣泄,而非觉悟成长。

一开始我就说明了,王广海不配拥有人物弧光,更不配拥有带升华性质的个人成长线...
因为他的高光点恰恰在于其“无成长”。
他从始至终都深陷于自我欺骗的生存策略中。
其爆发是这套生存逻辑彻底失效后的应激反应,非精神境界升华,他未能像其他角色那样完成从求生到抗争的人物转变...
而关于他是否知晓妻儿遇难,无论是不知道还是知晓真相但选择伪装,都符合他整个人生都在伪装的核心设定。
王传君赋予角色“无成长”,成就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感。
当其他角色完成英雄觉醒时,王广海却始终困在苟活-伪装-崩溃的死循环中...
这种未完成的救赎撕开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,使他成为了一个极为丰满,推动故事并引发深刻讨论的反派角色。